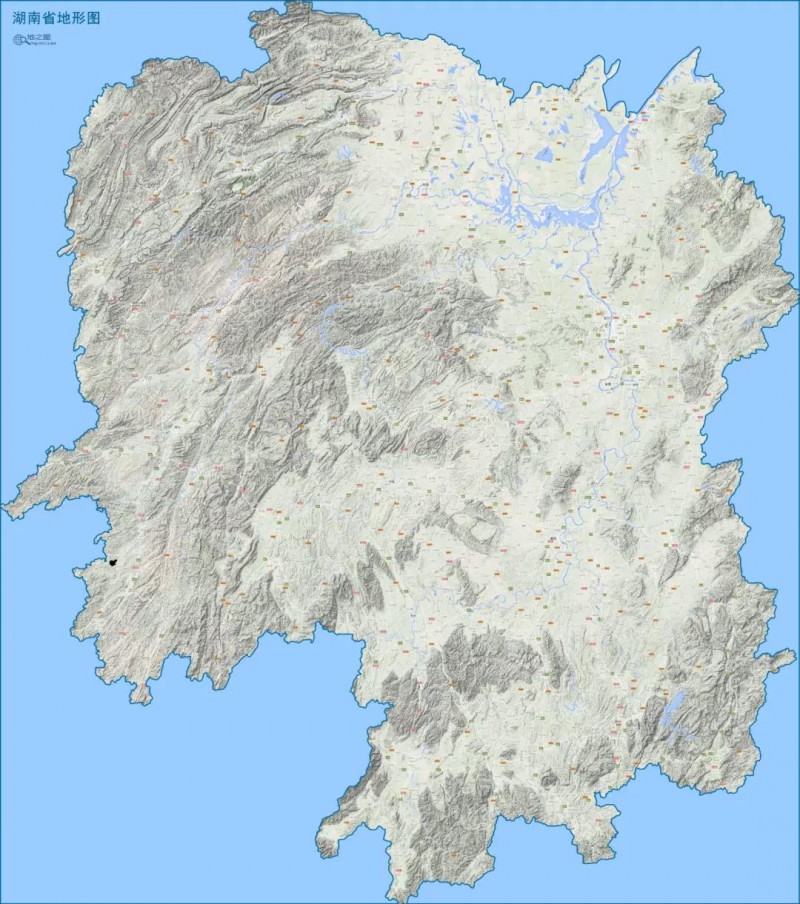
讲湖南百年风流,绕不开曾国藩。
关于时势与英雄,有很多说法,“天不生仲尼,万古如长夜”、“人类历史归根到底只不过是伟人的历史”……这些观点失之偏颇,但用在曾国藩和湖南上,却有几分道理。
湖南人的性格固然鲜明,但其在近代历史上的突然“发力”,单纯从地缘上解读显然缺乏力量,硬说是屈原或者王夫之的光辉照耀也有些勉强。
真正改变湖南的,是英雄与时势的风云际会。
世有非常之人,然后有非常之事。
命运的聚光灯扫过历史舞台的时候,总会有一些人突然冒出来,像雄鹰一样掠过历史的天空。曾国藩的崛起,就是一个典型案例。
千年来边缘、闭塞、蛮横、上不了台面的湖南,随着曾国藩的文治武功一同闯入历史舞台,湖南的历史乃至成千上万人的命运,也都被彻底改写。
我读了很多写曾国藩的书,要么晦涩艰深,要么云山雾罩,抑或不知所云的厚黑之学,其中唐浩明的《曾国藩》算是最经典的版本,仔细还原了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,如何够力挽天倾,成就不世之功的。
毛泽东说:“愚于近人,独服曾文正。”蒋介石评价曾国藩:“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,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。”两个敌对阵营的领袖,中国近代史的主角,对曾国藩的评价都是高度统一的完美。
事实上,比起历史上另一个公认完人王阳明,曾国藩连中人之姿都算不上。

湖南双峰 曾国藩故居
小时候曾国藩在屋里背书,恰好有个“梁上君子”想趁着曾国藩背完书休息后偷点东西,但没想到曾国藩这一篇文章翻来覆去读了十几遍也背不下来。
这位小偷忍无可忍,跳下来大骂:“这种笨脑壳,还读什么书!”骂完将曾国藩所读的文章从头到尾一字不落的背诵一遍,扬长而去。
曾国藩前后考了七次才以倒数第二的成绩考中秀才。且不说名冠天下,13中秀才,15中举人的大才子张之洞,就是和他后来的学生李鸿章相比,曾国藩的才气也远远不如。
如果单论事功,王阳明没法和曾国藩比。但在精神和义理层面,王阳明是曾国藩至关重要的榜样。如果没有王阳明文人领兵的先例,曾国藩也不会筹建湘军。
道理很简单,乔布斯和苹果的成功,我们可能没什么感觉,毕竟各方面差异太大,没有可比性。但当你眼睁睁看着任正非和华为的崛起,肯定会想:一个贵州佬能做的,我为什么不能?这就是榜样的力量。
苦读多年,终于中了进士的曾国藩,仿佛开了窍,十年七迁,官运亨通。但如果没有太平天国,曾国藩不会有那么大的名头,顶多是文章传世罢了,乱世给了曾国藩自主创业的机会。
1851年,太平乱起,烽烟遍地,湖南局势糜烂。咸丰情急之下,诏命在乡下丁忧的曾国藩帮助地方官员兴办“团练”,曾国藩历经千辛万苦,终于练成了一支一万七千人的队伍,踌躅满志,挥师北上。
谁知一败于岳州,再败于靖港,损失惨重,万念俱灰的曾国藩纵身跳进湘江,幸好被部属及时救下,一路风吹浪打、旌旗飘摇,仓皇逃回老巢。这应该是曾国藩一生之中最失意的一天。
然而不久后,湘潭传来捷报,“湘潭水陆大胜,十战十捷”,黄泉路近的大清王朝又看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。一时间,朝廷褒奖,绅民欢呼,湘军成了滔滔天下的中流砥柱。
此后曾国藩振作精神,重又踏上屡败屡战、艰难隐忍的封侯拜相之路,历经十年艰苦,终成不世之功。
就在曾国藩手握重兵,威望正隆时,年纪轻轻便名动天下,自诩通晓帝王术,“非衣貂不仕”的湖南老乡王闿运作为说客出现了。此公也的确有两把刷子,26岁就成了权倾朝野的重臣肃顺最依仗的幕僚,俨然半个帝师。
肃顺倒台前的半年,王闿运若有所觉,悄然离开京城,辗转南下,持帝王之学游说曾国藩,劝其割据东南,自立为王,与清廷、太平天国三足鼎立。然后徐图进取,收拾山河,成就帝王伟业。
游说过程中,曾国藩面无表情,一言不发,一边听王闿运讲,一边有意无意点着茶水在桌上比划。谈话中途,曾国藩临时有事出去。王闿运起身,看到曾国藩桌上写满了“狂”“谬”二字,一腔热血顿时冰凉,随即告辞回乡。
曾国藩究竟有没有心动,无人可知。只能从日记中知道:“傍夕,与王壬秋久谈(王闿运字壬秋),夜不成寐”。
王闿运之前,许多湘军重量级人物也曾或明或暗鼓动过曾国藩。胡林翼捎来左宗棠的一副对联,“神所依凭,将在德也;鼎之轻重,似可问焉”。
面对多年的至交好友,湘军核心人物胡林翼,曾国藩没有当场表态,只是说“容我考虑一下”。
几天后,曾国藩将对联改了一个字,回复给胡林翼,“神所依凭,将在德也;鼎之轻重,不可问焉”。胡林翼看了不再言语,几日后便返程湖北,几个月后病死武昌。
胡林翼走后不久,安徽巡抚彭玉麟也送来密信,“东南半壁无主,老师岂有意乎?”傲气如左宗棠、练达如胡林翼、淡泊如彭玉麟,三个性格迥异的湖南人,前前后后表达了同一种想法。
湖南这个地方也怪,政治情节特别强。治世时“学得文武艺,卖与帝王家”,乱世就苦学人君南面之术,图谋做帝王之师。这既是湖南人的优良传统,但有时也会失之于过于功利。
我和湖南卫视的灵魂人物魏文彬很熟,他是文化湘军的代表人物,十多年前他请我给湖南广电做战略策划,也做了一场演讲。
讲演完以后,老魏突然冒出一句话:“志纲啊,你为什么不从政呢”?在他看来,有才华却不去出将入相走仕途,简直太亏了,这就是典型的湖南人心理。
1864年,湘军攻破南京,恢弘华丽的太平天国轰然坍塌,曾国藩个人威望到达巅峰。湘军气焰熏天,收拾金瓯一片,分田分地真忙,千年古都南京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浩劫,长江之上来往的都是湘军将领装满子女财帛的船只,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内,湖南人中都流传着一句话:“到金陵发财去”。
一片大好形势下,曾国藩更加忧心忡忡,清廷、太平天国、湘军三股势力已去其一,对于清廷来说,湘军的存在已然尾大不掉。王闿运的出现更让曾国藩警觉,这种狂生都来劝我称帝,朝廷会怎么想?
果不其然,封赏与敲打接踵而至,慈禧早已摆好卸磨杀驴的架势,湘军内部群情激奋,曾国荃率多位湘军高级将领齐聚曾国藩府邸,图谋重演“陈桥兵变、黄袍加身”的戏码。
一片劝进声中,曾国藩闭门屋内,一言不发。僵持良久,曾国藩差人送出一副对联,“倚天照海花无数,流水高山心自知”,所有人见事不可为,才默然散去。
下定决心不反,曾国藩马上开始自剪羽翼,首先开刀的就是自家人,曾国藩强令曾国荃解甲归田。曾国荃带着一腔愤懑和满船金银财宝,返回湘乡老家,曾国藩赠给他一副对联,“千秋邈矣独留我,百战归来再读书”。
曾国荃走后,横扫江南、威震天下的湘军也迅速被裁撤,峥嵘岁月瞬成过眼云烟。自断牙齿和羽翼的曾国藩,赢得了清廷的空前信任。千百年来,功高震主又全身而退者,寥若星辰。
世上有两种人可以成大功、立大名,一种是情商极高、修为极深的人,能忍常人所不能忍;还有一种是天赋极高、能力极强的人,能为常人所不能为。曾国藩属于第一种人,而左宗棠属于第二种人。
左宗棠一向自负才高,以当今诸葛亮自比,谁知屡试不第,一怒之下蛰居乡间以教书为生,直到48岁才得到天子钦点,协助曾国藩办理军务。
彼时李鸿章也在曾国藩麾下,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其三初次聚首,三人能力非凡,又性格迥异。
李鸿章看重功名,曾放言“一万年来谁著史,三千里外觅封侯”;而左宗棠更看重事功,落魄时常以“身无半亩,心忧天下;读破万卷,神交古人。”自勉。曾评价李是“拼命做官”,功利心太重,对左则推崇备至。曾左虽有矛盾,无非是“一时瑜亮”的相爱相杀;而左李之间,则是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的互相倾轧。
左宗棠寒微时名头已经极大,胡林翼称其为“近日楚才第一”。风烛残年的林则徐乘舟路过湖南时,在湘江边上专程滞留一天,特地等候自诩今亮的左宗棠。
两人一见如故、相见恨晚,彻夜倾谈,纵论国家大计。这是他们初次谋面,也是最后一面。
晚年的林则徐世事看透,只有一事放心不下。他说,“吾老矣,空有御俄之志,终无成就之日。数年来留心人才,欲将托付重任”、“东南洋夷,能御之者或有人,西定新疆,舍君莫属”。
两人见面不到一年后,林则徐溘然长逝。
25年后,垂垂老矣的左宗棠终于秉承林则徐遗志,力排众议、舆榇出关,一举克复新疆,为华夏子孙保住了160万平方公里大好河山。此等壮举,就决于二十五年前的一个寒冷冬夜,湘江边的一条小船之上。
1983年胡耀邦去西北视察时,曾引用“大将筹边尚未还,湖湘子弟满天山。新载杨柳三千里,引得春风渡玉关”,这首诗让当时刚从兰州大学毕业的我印象深刻。
后来我多次去新疆,沿途还能看到很多合抱粗细的左公柳,心中不由感慨,湖南蛮子确实了不起。
后平定新疆的王震,最推崇左宗棠,再加上王震也是湖南人。我在兰大读书时,学校里有位专门研究左宗棠的老教授。王震专门请他吃饭,暗示他来写一下湖南人的风起云涌和当代左公的功业,究竟写没写尚且不论。但从曾国藩到左宗棠,湖南人开始走上时代中央。
曾左之后,看似烟消云散的湘军,实则给湖南埋下了天翻地覆的种子。
从古至今,湖南人就有重视教育的传统,千年以来岳麓书院弦歌不绝。湖南虽然地域广阔,但肥沃之地不多,大部分土地贫瘠,出产不丰富,又加之人多,故而从整体上来说民生贫困,国家从湖南所得之税收也少。
文书上说,湖南全省一年税收不及江南一大县,上马从军或下马读书,成了很多湖南人改变命运的唯二办法。
一位湖南博士曾给我讲小时候父亲怎么培养他读书的。他父亲站在水田边,拿着一双草鞋和一双皮鞋教育儿子,话也很简单,好好读书就能穿皮鞋,不读书就和你老爹一样,穿着草鞋顶着赤日下地受罪。
他深受震动,终于通过不懈读书走了出来,而这样的故事从古至今,在三湘大地上遍地皆是。
当年苦于条件所限,只有少数湖南人才能读书。然而几十万盆满钵满的湘军裁撤回乡,一夜间完成了原始积累,他们开始在家乡置田地、聘塾师、教子弟,短短一二十年之内,三湘大地开始兴起一股教化之风。尤其在洞庭湖一带,更是文化昌明,全国各地有才华的人都愿意到湖南去教书。
讲到湖南的风气之开,这还有一个人物不得不提,就是陈寅恪先生的爷爷陈宝箴。
陈宝箴在湖南巡抚任职期间,积极推行新政,开设时务学堂,出刊《湘学报》,整顿吏治,革除旧习,启用和推荐维新人物谭嗣同、梁启超等,可谓营一隅为天下倡。
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,湖南成了全国最有生气的省份,教育事业发达,新式学堂之多居全国前茅,时务学堂尤为著名。
《湘学报》名满海内,陈宝箴功不可没,其人虽仕途蹇塞,文脉却绵延不绝。其孙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、古典文学研究家、语言学家。
陈氏一脉虽不是湖南人,却和湖南渊源甚深,湖南是陈寅恪的第二故乡。解放后,陈寅恪也遭受到了政治风波的冲击。
当时陶铸(湖南祁阳人)任中南局书记,出于对陈的尊敬和爱护,时到中大去访谈,嘱有关方面给陈以照顾。
由于陈双目损坏,陶亲自关心他的助手配备和眼疾治疗,还嘱咐在他的院子里修一条白色通道,让他闲余散步时不至摔倒。殷殷关怀成了知识界的佳话。这也算陈寅恪晚年与湖南人的一段缘份吧。
除了物质条件大发展,曾国藩也为湖湘文化注入了新的精神内涵。战争把曾国藩和湘军推到时代的前列,南征北战让世代居住在穷乡僻壤的农民有了外出闯荡的机会。
见识过人世间最复杂最严酷的斗争后,他们的眼界大为开阔,胸襟大为拓展,见识大为提高。湖湘文化在最广大的层面上有了质的提升,国家、天下、道义等原本只是少数人关心的话题,开始出现在很多普通湖南人的嘴边。
千百年来,湖南人形成了独特的性格特质,而曾国藩、左宗棠等人的横空出世,让大批湖南人“走出去”,把财富与知识“请进来”,给湖湘勃兴添了最后一把火。
湖南人继承自远古楚人奔放浪漫、天马行空式的自我主义逐渐提升为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意识;经世致用的功业追求逐渐变成忧国忧民、救世拯时的忧患情怀;轻生任侠的血性变成为理想而献身的牺牲精神;霸蛮易怒的祖传性格变成了顽强果毅的坚执定力——从物质到精神、从眼界到心胸,湖南终于彻底升华了。
如果说曾国藩是湖南百年风流的上半场代表人物,他去世21年之后,下半场的代表人物毛泽东正式登场。

17岁的毛泽东外出读书临行前,改写了西乡隆盛的一首七言绝句:“孩儿立志出乡关,学不成名誓不还。埋骨何须桑梓地,人生无处不青山。”这是典型的立志诗,湖南人的经世致用、壮怀激烈已经有所体现。
而在青年毛泽东的一方天地里,曾国藩也占有独一无二的位置,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把他对曾国藩的崇拜悉数传递给了这位学生。
毛泽东早年曾经下苦功研究过曾国藩的著作。曾国藩的治军方略和处世之道深深地触动过毛泽东的心灵,使他发出了“独服曾文正”的慨叹。
当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后,很多人攻击他不懂军事。这种说法其实很可笑,湖湘天生重血性,再加上湘军余威犹存,毛泽东在湖湘这片江湖上学了很多东西,比如拿家喻户晓的“三大纪律,八项注意”与曾国藩编写的“行军歌”对照,会发现前者简直就是后者的翻版。
而且毛家一直有着从军打仗、驰骋疆场的家族传统。毛氏家族的始祖毛太华便是“以军功拔入楚省”。此后,毛太华的子孙秉承他的刚毅和血性,投身行伍、闯荡天下者代不乏人。
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崛起后,大批毛氏子弟加入湘军,形成一股从军潮。
在这样有军事传统的家族中成长,毛泽东耳濡目染,不可避免地接受到尚武精神的影响。据韶山的一些老人回忆,毛泽东从小好角力,喜欢玩打仗的游戏,对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》、《说唐》等描写战争的书爱不释手。毛泽东的思想、志向和军事才华,都和湖南这片土地有很深的渊源。
国共战争中,毛泽东和蒋介石正面对决。国共两党的许多著名将领都受过曾国藩军事思想的熏陶。蒋介石是曾国藩的狂热信徒,但蒋更多学的是私德,而毛泽东则是从学习到扬弃。
蒋介石身边浙江人居多,而毛泽东身边则围绕着一大批优秀的湖南人,刘少奇、任弼时、彭德怀等,结果是霸蛮的湖南人打败了灵秀的浙江人。
从曾国藩建湘军到新中国成立,短短一百多年。湖南一地汇聚澎湃汹涌的能量,涌现出的一批风流人物,为中国境内所仅见。
在主流口径中,几乎众口一致的认为现代中国发展于文化中心——北京,或沿海对外中心——上海和广州,湖南则被普遍描述为一个偏僻落后,需要加以启蒙的内陆省份。
然而先后诞生曾国藩与毛泽东的湖南,完全够格来讲述古老中国的百年风流,湖南人波澜壮阔的一百年,改变中国的历史,也重塑了湖湘精神。
(本文系转载,原文标题:“湖南到底怎么了:无官可当,无名可出,无事可做”


